《教育发展研究》
2019年第24期

摘要:教育工作者最重要的特质是具有一种“教育精神”,欧博abg并能将理论与实践相融合,因此没有必要区分教育家与教育学家,因为在其内在特质上,两者是完全一致的;也不必把教育家视为一个高不可攀的层次,只要他们具有教育精神并坚守初心,他们都在履行教育家的角色。而教育精神包括“无差别性”、“真诚性”、“导引性”和“反思性”四个方面。今天提出并讨论教育精神,旨在从规范性维度应对教育活动的不确定性,并重构教育共同体的专业承诺。
关键词:教育家 教育精神 规范性维度
“教育家”是一个近年来反复出现的词,然而,当我们在谈论教育家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在谈论一种行为还是一种类属?是谈论一个概念还是一种态度?
一、教育家的定位
从日常经验的理解看,教育家应该是从事教育理论与实践探索,并恪守良善教育价值的一个群体。韩愈《师说》曰:“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在这里,教师的职责是传道受业解惑。不过,中国古代有“经师”与“人师”之别。东汉郭林宗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 。“经师”,即“教书匠”,“人师”,乃“教育者”。意思是能以其精湛的专业知识传授他人(做经师)并不难;而能以其渊博的学识,高尚的人格修养去教人如何做人(做人师)就不易了。按照这种理解,传道受业解惑者仅是经师,人师则对教育者本身的人格提出了要求。在教育过程中,知识与技能的传授是相对容易的,而心灵的熏陶是极其困难的,后者需要教育者的身体力行,德行垂范。
在英文中,教育家有两个相近的词来指称:educator或educationist,前者更多指执教的教育工作者;后者更多指从事于理论工作而非具体教育活动的人,不过educationist是一个很少被使用的词,而我们也很难对两者进行严格区分。1993-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曾经出版4卷本的《Thinkers on Education》,专题介绍世界各国最负盛名的100位教育思想家[1]。2001年,美国著名的劳特里奇(Routledge)出版社也出版了两本书,分别是《50位重要教育思想家:从孔子到杜威(Fifty major thinkers on education: from Confucius to Dewey)》、《50位现代教育思想家:从皮亚杰到今天(Fifty modern thinkers on education: from Piaget to present)》。对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书与劳特里奇出版社的书,其中所选的100位教育思想家有很多重叠,虽然编撰者不同,但判断标准类似,就是看其对教育发展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是在教育理论上,其次是由教育理论传递给教育实践并通过受影响者(如教师)最终影响教育实践的。当然,我们还可以发现这100位教育思想家其实远不仅是通过其思想影响教育的,其中不乏实践传统的开创者,例如孔子开启了中国古代教育的私学传统;夸美纽斯不仅提出了班级授课制,还亲自为孩子编了《世界图解》;杜威创办了芝加哥实验学校——这所实验学校由1896年持续至1904年,并由此深刻影响了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则推动巴西扫盲识字运动,并曾担任巴西人口最稠密的圣保罗州的教育部长。他不仅通过著作《被压迫者的教育学》为穷人的教育而呼吁,同时也花费大量精力审议课程设置和提高巴西教育工作者的工资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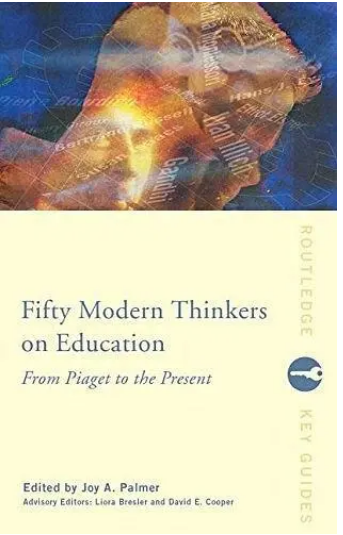
不过,很长时间来,我们确实难以定位教育实践家与教育学家,而只是习惯地将两者进行说辞上的区分。也许,有人认为,教育思想家是理论的倡导者,是思想的传播者,是精神的感召者,是行动的呐喊者,欧博官网但不一定是实践的参与者。换言之,教育思想家或教育学家只是在解释教育,而问题在于改造教育。但是,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是否存在着真正的对立?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难道对世界每一个解释不都已经是对世界的改变了吗?对世界的每一个解释不都预设了解释是一种真正的思之事业吗?另一方面,对世界的每一个改变不都把一种理论前见(Vorblick)预设为工具吗?[2]因此,我们不仅需要通过实践改变教育现实,更需要对教育活动提出新的解释,正是这种新的解释或理论洞见,形成了我们改变教育现实的观念和方案。教育研究是从探询“教育是什么”开始的,这种探询也贯穿了整个教育思想史。尽管这个问题没有至今没有确切的答案——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答案,但不正是通过以各种方式回答这个问题,才引发教育事业的一次次变革吗?不正是由这些不同的回答,启迪无数教育实践者产生改造现实的意愿并付诸于实践的尝试吗?
2017年,英国伦敦大学卡尔·曼海姆讲座教授波尔(Stephen J. Ball)出版了《作为教育家的福柯(Foucault as Educator)》一书,对福柯的教育思想作了分析。波尔利用福柯的思想资源,阐述了福柯作为教育家在实践中可能的意义或与实践的关系。他勾勒了福柯所称的“自我的美学”的轮廓,即福柯后期作品中提到的一种“自我教育”或“自我形成”的形式,也就是说,有可能成为某种“你不是”的人,这是一种试图把教育想象成 “越界”和“审美自我”的精神。
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实不存在教育实践家和教育学家之分。我们所谓的教育家一定不是纯粹的实践者,任何有意义的实践本身即包含了理论的见解。如果只是基于自己未明晰的教育意见而进行盲目探索,即便在某一时刻获得成功,也不过是经验或惯例的偶然胜利,难以走出区域性条件的约束。只有对教育进行系统思考,并以这种系统思考的理论视角观照教育,从而着手改造教育现实的实践者,才会在今天复杂的教育境脉中获得成效。同样,系统阐发理论见解的教育研究者,即便没有亲身实践,由于其对教育实践者的思想影响,同样也在改变现实,这也是教育家之所为。其实,如柏拉图所认为的,没有什么比理论本身更具实践性,古希腊人将那些专注于沉思生活的有智慧的人当作值得尊敬的楷模。因此,教育家首先是对教育活动进行深思并提出解释的人。
二、教育精神与教育家
当然,人们常常期盼教育界的爱因斯坦,期望能有爱因斯坦式的天才给予教育颠覆性的理论想象。可是教育领域却非常不同:一是其特异性。教育活动的多样性使得实证主义者们妄称的可重复性难以兑现,除非是同一批对象的重复实践,但这有意义吗?事实上,教育研究中几乎不存在作为自然科学典范的物理学意义上的可重复研究结果,即便著名的美国田纳西州的小班化实验,在程序上也有可质疑之处。而正常的教育研究给出的是基于统计学意义的趋势性说明,遵循概率性原则,非确定性原则。二是教育研究更关注教育的长期后续效应。教育活动从来是慢的实践,个体的生长周期决定了教育实践的慢性。物理实验或许可以在一晚就可完成,教育实验却常常数月甚至数年也看不到确切的结果,所以不可能呈现狂飙突进的景观。三是教育家是将对教育内在规律的探索与本己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人。所以,如果我们期待教育家能够像物理学家一样对教育过程作出精准的预判,可能会很失望。但是,对照社会科学中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社会科学中唯一可以授予诺贝尔奖的学科),我们不也可以看到同样有趣的现象——几乎没有一位经济学家预见过频发的金融危机或经济乱象,这是经济学家的无能还是经济活动本身的复杂性所致?
事实上,我们不必把教育家视为一个高不可攀的层次,正如我们不会认为唯有爱因斯坦才是科学家一样——毫无疑问,欧博爱因斯坦是伟大科学家的标杆,但其他达不到爱因斯坦高度却同样执着的科学探究者,只要其具备科学精神并进行不懈的科学探索,就是一位科学家。
这里涉及到了科学精神。让我们回顾一下大家熟知的、由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Robert K.Merton)所提出的科学精神。1942年,默顿发表了一篇题为《科学的规范结构》的重要论文。在这篇文章中,他给科学精神下了一个定义:科学的精神气质是有感情情调的一套约束科学家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这些规范用命令、禁止、偏爱、赞同的形式来表示。它们借助于习俗的价值而获得其合法地位。这些通过格言和例证来传达、通过法令而增强的规则在不同程度上被科学家内在化了,于是形成了他们的科学良心。[3]默顿又提出四种惯例的规范作为科学精神的组成。其一是普遍性(universalism),对正在进入科学行列的假设的接受或排斥,不取决于该学说的倡导者的社会属性或个人属性,也就是说与他的种族、国籍、宗教、阶级和个人品质无关。其二是共有性(communism),任何科研成果都是社会协作的产物,并且应该分配给全体社会成员,发现者和发明者不应据为私有。其三是无偏见性(disinterestedness),反对欺骗、诡辩、夸夸其谈、滥用专家权威等等。其四是有条理的怀疑性(organized skepticism),坚持用经验和逻辑的标准,审查和裁决一切假说和理论,而决不盲从。仔细分析这四种规范,可以发现科学精神即是作为一个真正科学家的精神,是科学家特质的体现,并反映在其科学探索活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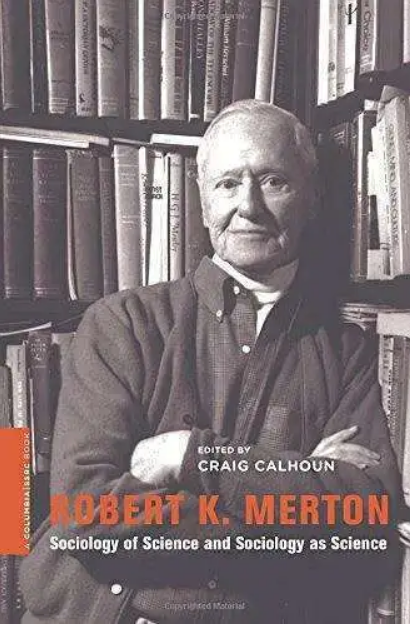
总之,科学精神是科学家群体行为规范所体现的一种精神气质,它不能单纯依靠任何学术规定去简单地定义或解释,而只能通过了解科学规范而理解。
其实对于从事教育活动的成员群体来说,是不是同样有一种共同的气质,这种共同气质通过教育家共同体的思想、实践推理及行为惯习表现出来,是具有确定效用的价值和规范构成的复杂体系,也是从事教育活动的人的行动要旨或共同体要旨,它对教育工作者具有约束力,我们不妨称之为“教育精神”。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精神是指人的精气、元神,如汉王符《潜夫论·卜列》:“夫人之所以为人者,非以此八尺之身也,乃以其有精神也”;或是指事物的实质、要旨、事物的精微所在,如宋王安石《读史》诗:“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海德格尔则说:“肉体的所有真正力量和美,剑之稳当与冒险,还有理智之老实与机灵,都植基于精神之中,它们只有在当下精神的有力或无能中,获得提高或陷于崩溃”[4]。虽然国家与社会的情形不同,但教育精神却是相通的。教育事业需要教育者,他必须是有德性(virtue)的人。在意涵指向上,教育精神与科学精神是互通的。
就这个意义而言,“教育的工作”不应被看作是关于教育问题的工作,而更应被描述为“关于人的成长的工作”,即是关乎个体如何能获得社会性价值和知识理解力,身心健康的融入社会,具有德性(Virtue)地参与社会生活并创造新的价值的工作。英国教育哲学家彼特斯认为“教育”的核心标准或基本用法包括:第一,在具体目标上,教育所获得的 ‘成就’必须是‘善的’和‘有价值的’;在终极目的上,教育必须帮助人们获得健康的‘生活方式’,树立一般的世界观,而不局限于纯粹功利或职业目的的达成;第二,在方法上,取得成就的教育方式必须是“道德的”或“无可非议的”;第三,在过程中,欧博娱乐教育必须是有利于学生自主性的确立和发展的。
在彼得斯看来,“受过教育的人”拥有三个独特的地方,即三个标准:(1)价值标准:“受过教育的人”应该生活得有价值。这体现他的行为表现上,参与的社会活动中,以及价值判断和情感里。(2)知识标准:“受过教育的人”必须具备知识(而非技能),还必须能够理解知识背后的原理。(3)对知识应持有的态度标准:“受过教育的人”所掌握的知识不应是“僵化的”。他能够用所具备的知识和对世界的理解来改变自己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5]。
从起源上看,教育是保障人类自我延续和进化的一项古老而不可或缺的活动。到今天,它已呈现为一种制度化的规范性活动,并指向每个个体的学习与发展,且这种发展在机会上应是公平的。既然在发展机会应是公平的,那么教育精神首先是其无差别性,即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无论其种族,无论是富裕还是贫穷,无论是健康还是疾患,无论是美丽还是丑陋。但是,无差别性并非是采用同样方法对不同的人进行教育,即不是“均平”。因为发展机会的公平不是结果的均等,所以与无差别性伴随的是人的个性化发展的机会,即主张针对不同的人采用与其个性相宜的教育方式——因材施教。
其二是真诚性,反对欺瞒、哄骗、诱导,甚至用谎言说教。所谓“真诚”, 是指坦白而直率地展现自己于他人, 而不是隐藏或添加某些东西以把自己展现为与实际情况不同的人。真诚之人的言行是他们真正相信的事情。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全部教育的关键在于选择完美的教育内容和尽可能使学生之思不误入歧途,而是导向事物的本源”。……“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6],面对赤裸裸的灵魂,任何欺瞒或伪装都失去其意义。其实早在雅思贝尔斯之前很久,苏格拉底就赞同将教育理解为使灵魂转向真理的活动。谎言只会让灵魂转向邪恶,而虚假的东西必然带来被欺瞒的灵魂,被欺瞒的灵魂即便握有巨大的力量,也无益于由每个个体共建的社会,恰如孟子所说:“诚者,天之道;思诚者,人之道。”(《孟子·离娄上》)
其三是导引性。即指导受教育者的价值与道德的向善,引领学生的自主发展和理性成熟。古汉语“教”的本意是“使之上以施、下以效”,指由上对下的引导、示范作用,所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敎”(礼记·中庸》)。《《孟子·公孙丑上》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强调做事精细,强调精益求精。孟子更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的说法。无疑,孟子的大丈夫气概的阐述对今天教育目标的确立仍有重要意义。英文的教育(education)源于拉丁文的educrae,词根是“ducare”,有引导出的意思,也就是力图将良善的东西引导出来。但在对教育活动的理解上,存在“积极教育”与“消极教育”的分野。
积极教育主张对受教育者进行干预,以改变其初始可能性或自然特性;而消极教育则主张呵护受教育者的天性,使其能自然生长。前者如黑格尔认为:“教育、教养与管教就是改变个体的自然欲求,而使冲动获得其理性的限制(人们回想一下身体及其各部分——身体的活动就可以理解了)。管教首先就产生了自然的兴趣,它摆脱了自然的意志。冲动抛开了自然属性的形式。这首先是通过服从发生的( 谁没有学会服从,谁也就不会命令) 。……。对主人的畏惧是智慧的开始。自然的东西在我身上就动摇了,由此自然就流动起来。”[7]后者如卢梭则认为:“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8]。所以他主张:“最初12年的教育应当纯粹是消极的,它不在于教学生以道德和真理,而在于防止他的心沾染罪恶,防止他的思想产生谬见。”[9]卢梭的《爱弥儿》是一本文采斐然、充分表达其教育观念的教育小说。但如果将其规诫完全付诸实践,则可能引向灾难。裴斯泰洛齐在教育他儿子雅各布的过程中痛苦地证明了这一点。[10]这个4岁的男孩通常可以凭自然冲动行事,但他的父亲老是时不时地在不作任何解释的情况下压制他的自我中心感,希望在这个意志冲突的孩子身上萌发一种法律意识。实际结果是,孩子再也弄不明白他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父亲,这个父亲有时非常开明,有时却是一个无法忍受的暴君。雅各布生来就脆弱的神经结构受到了无法挽救的损害。
由于人的发展的差异性,导引性一个基本要求也是因材施教。黑格尔与卢梭呈现了针锋相对的教育观念,一个是强调对自然性的管制,认为管制才能使原本凝固的自然性流动起来,获得改变;另一个是强调对自然性的坚持。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过程观,也代表了对教育活动完全不同的理解。但其目标也许是相近的,都面向人的成长。
其四是反思性。Reflexion ( 返回、反映、反思) 概念可以追溯到拉丁语reflecto ( 返回) 一词,即在其专业生涯中不断反思并自我提升。为了获得普遍依据之可能,反思概念通过剥离外部世界,进入了主体自身;也正是通过这一反思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了,要获得普遍依据之真正可能,就需要走出自身之外。由外至内,又由内至外,构成反思活动的循环。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过的”;同样,对于从事教育的人来说,未经省思的教育实践是不值得做的。胡塞尔曾说: “在宗教中是情性的正直,在哲学中就是智性的真诚。我一生都在为这种真诚而战,实际上是搏斗。别人早就满意的地方,我一再重新追问并仔细检查背景中是否确实没有一丝不真诚。我所有的工作,即使是今天的,也只是一遍遍地检查和审视,因为我提出的一切毕竟都是相对的。人们必须有勇气承认并且说那些人们昨天还认为是真的,但今天看起来是错误的东西就是这样的错误。”[11]这种善于反思的态度,或许是我们所有教育研究者应该遵循的真诚态度。而这恰是教育精神的体现。
概言之,“无差别性”、“真诚性”、“导引性”和“反思性”构成教育精神的四个特质。我们可以继续设想有其他的特质,但这四个特质作为教育家或教育学家的基本精神,影响或衍生着其他特质,反之,则不成其为教育家。所以,当我们讨论教育家时,我们是指一群具有“教育精神”的人的工作态度、工作要求和工作方式,我们为之而折服。王阳明说:“天地虽大,但有一念向善,心存良知,虽凡夫俗子,皆可为圣贤。”同样,对教育活动而言,凡有教育精神并坚守初心的践行者,即可谓之“教育家”。
三、教育精神的意味
然而,为何要从“教育精神”意义上界定教育家?难道我们的日常认知或常识不能感知教育家的存在吗?教育是一项看似平凡的活动,也许很多校长都在内心中寻求办学的突破方向,但同样有很多校长或许被各种口号或流行话语所蛊惑。也有人喜欢用诗化的语言描述教育,例如:“教育就是一棵树摇动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但是,这种描述也虚化了教育活动的可能性。因为教育活动依赖具体的路径和方式。诗化和虚化,在针对教育活动的描述中,成为一个分币的两面。当我们用诗化的意象刻画教育活动时,一定程度上就将其焦点虚化了。
英国教育哲学家怀特(John White)在《再论教育目的》的前沿中说:“至少在过去25年中,说到教育的内容,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课程’而不是‘目的’。在学校委员会和其他机构的庇护下,学校充满了源源不断的学习计划、课堂作业,关于各种课程的教科书和论文。”[12]这不也是我们当下基础学校面临的现实场景吗?
这就需要回溯教育的本源。我们希望学校是一个让学生认识自我,发掘自我潜力的地方。我们希望每个孩子能够正确认识自我的价值,这不仅是为了维护他们自己,同时也为维持一个更长远的目标,使他们能够对社会贡献他们的价值。换言之,学校需要关心每一位学生的精神生活。而且,这种精神生活不仅是“道德的”,也是“认知的”,还是面向“实践的”。我们倡导德育为先,但学校的“道德文化”还不能涵盖学校文化的深意。现代社会充满压力和危机,每一代学生都会面临人生前行的十字路口,彷徨迟疑、焦虑恐惧在所难免。学校不是提供解决问题的既有答案,而是为学生扩宽思考问题的视野,让学生学会明辨是非,培养其优秀气质和良好习惯。这种对精神生活的关怀不是需要具有某种特定精神的人的身体力行吗?即一个示范体或催化体,德里达在《论精神》中谈到“精神是火焰。一种去点燃着的或自行燃烧的火焰:同时是二者,既是一个又是另一个,彼此相与。二者在共燃本身中的共燃”[13]。

可是谁去点燃?当然是具有教育精神的“教育人”。正是在“点燃”和“共燃”这一点上,教育精神的意义最为凸显。这里人们自然会想到有关教师“蜡烛”的隐喻,然而这却是一个不当的隐喻,因为“教育人”的专业性在于用自己的教育精神去唤起(共燃)学生的理解和领悟,引燃其内心的善良与真诚,其过程不是将自己变成灰烬,而是与学生共同成长,所谓“教学相长”的意义即在此。但是“教育人”如何能够意识到培养学生的过程,也是自己成长的过程?《论语·学而》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需要一种时刻省思的品质,所以“反思性”即是共同成长的条件。
然而,为何在今天,我们需要召唤“教育精神”?实际上,这是试图从规范性维度讨论教育活动正当性的一种努力。
我们正身处一个变幻莫测的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高度不确定性或偶在性使得教育问题变得尤为复杂难辨。偶在性是指,在即将到来的下一步体验中,被指向的可能性总是有可能与期望中的可能性不一致[14]。这首先体现对教育一系列核心问题的思考中,如:培养什么人(教育目标)?为谁培养——当然不是为某个个人或某利益集团而培养,而是为促进社会福祉及个体的健全发展而培养(教育目的);培养人的目标是普适的还是分殊的(目标分类)?谁来培养(教育主体)?如何培养(教育途径)等问题。这些问题尽管是教育的永恒话题,却在不同语境中不断累积其复杂性;其次,由于学校教育愈来愈跟个体的生活机遇及社会分层密切关联,致使教育的功利趋向愈发彰显。教育虽然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却越来越受制于社会环境,甚至解决教育问题的途径不在教育系统本身,而在社会的其他系统中。所以既有教育系统内部的复杂性,更有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导致系统与环境的双重纠缠。由此,如何化解教育系统的复杂性成为一个严峻的问题。
而德国社会思想家卢曼(Niklas Luhmann)也是从化解复杂性的视角来认识规范性的。卢曼提出,现代社会复杂性的增长要求落实结构化,其规范与个人道德不存在必然关联,即在系统分化社会中,不同的系统将按照不同的规范运行,不可能存在一个从个体道德出发的、能够适用于单一社会系统的乃至整个社会的规范。他认为:“规范就是反事实稳定的行为期望( counterfactually stabilized behavioural expectations) 。规范的意义具有无条件的有效性,因为这种有效性的体验和制度化可以与规范实际上是否得到遵守无关。”[15]不同的社会系统,例如宗教、艺术、政治、经济、道德、法律、教育、科学、生态等,都将创造并不断创造着属己的规范。规范性是社会系统通过系统之间的耦合后对人的诉求予以吸纳之后的稳定建构,但这并不是说所有人对“环境”的期望都能变成规范:“规范有效性的基础实际上就在于,不可能在任何时候把每个人的每种期望都纳入考虑。因此,规范有效性的基础根本上就在于期望领域的复杂性和偶在性,而其功能就在于对此进行化简。”[16]
真正与规范性对立的不是事实性,而是认知性:在遭遇失望时,我们只能在规范性和认知性两种立场中作出有意义的选择,而不是在规范性和事实性之间作出选择。因此,我们不能牵强地把认知期望和规范期望之间的区分转换成古代关于存在和应然之间的事实性(或逻辑性)对立[17]。规范性一个突出的方面就是相对于行动者的权威性和约束性,一个规范能够对我们提出某种命令、支配和要求,或者向我们推荐某个东西,引导我们去做某件事。传统上,规范性具有:(1)义务性。规范性所具有的约束性力量往往意味着某种程度的“义务”——只有履行了这样的义务,或者说遵循规范性的要求,才能顺利实现某个目标或达到某种效果。(2)超时空性。尽管规范性是在具体时空和情境下提出的,但规范性要求的效力往往是超越具体时空的。如果一个规则或规范性陈述是正确的,那么它将不仅适用于过去和当下情境,对于未来尚未发生的情况也应同样适用。[18]
规范性具有的义务性,实际上包含了一种承诺。规范性承诺具有以下基本结构:(a)有产生承诺的条件——由于满足条件而引起承诺;(b)只要满足引起承诺的条件,某人就会对某件事作出承诺;(c)承诺与理由相关。假定已经对Φ做出承诺,那么有一个(规范的)理由可以保证一个Φ或一个Φ导致承诺不再发生的条件。[19]
阿兰·米勒(Alan Miller)认为:“规范性首先是诸如判断、信念、陈述、要求之类的可以是对或错的事情。规范陈述的核心情形是这样的,一定意义上,存在某个或某些行动者做某事的理由。在这一语境中,‘做某事’是在广义上使用的,因而它不仅可以涵括某些方式的行动,也能涵括相信某事、欲望某事、以某种方式感受,等等。同样,它也可以涵括限制以某种方式行事。”[20]
一个人可以通过根据情况放弃信念或意图来履行因信念或意图而产生的承诺。这样一来,一个人就不再满足承诺发生的条件。很明显,一个人不能通过不再承诺来摆脱承诺所带来的承诺。实践本质上是规则控制的活动,参与实践需要遵守其管理规则,即任何从事该活动的人都必须遵守规则。承诺只能在给予和接受它们的实践中才能给予和接受,必须有规则来规范什么是做出承诺,以及做出承诺之后会发生什么。这些规则从来没有被明确地要求形式化,重要的是,人们的行为要像有这样的规则一样,要有一致的期望。服从规则的标志之一是把规则规定的那种行为当作应该做的事来对待,因此,把不符合规则的行为当作可以批评的。
实际上,教育活动一直是一种高度规范性的社会活动,因而从一开始就对从业者提出了专业准则,只是这种准则被以不同的隐喻所表达,这些隐喻虽然并没有将其规范要求具体呈现,却以默会的方式昭示从业者的职责。我们认可某人在教育上的专业性,是认为他身上体现了教育活动的诸规范,不仅在理论上阐述并在实践上弘扬这些教育规范,换言之,它们也构成教育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准则。因此,对“教育精神”的分析,也是重建教育共同体的努力。
正是时代挑战带动并引发了关于“教育家”的精神要求。当我们把教育的核心问题,放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境况中思考时,我们面临比以往任何时代更多的困惑与挑战,这种挑战的由来,不仅在于教育系统的分化导致的风险性或复杂性增加,也在于教育系统外部环境的多样性导致的偶在性。这种情境已不能仅靠认知性选择加以克服,由此自然需要从规范性维度加以审视。
在一个功利教育盛行的年代,我们呼唤“教育精神”,更是将“教育精神”作为对培养人活动的志业承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参考文献
[1] 中文版名为《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四卷本) [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
[2] [法]F.费迪耶等/辑录、丁耘/摘译,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哲学译丛》[J]2001年第3期,第53页。
[3] [美] R.默顿/文,林聚任译,科学的规范结构.《哲学译丛》[J]2000年第3期,第56页。
[4] [德]海德格尔著,熊伟、王庆节译.《形而上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7页
[5] 参见彼得斯/文,王承绪译.教育与受过教育的人[C].王承绪、赵祥麟.《西方现代教育论著选》 [A].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6] [德]雅思贝尔斯著,邹进译.《什么是教育》[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4页
[7] [德]黑格尔/文,李文堂/译.《法哲学演讲录》导论,《世界哲学》[J]2017年第3期,第47页
[8] [法]卢梭著,李平沤译.《爱弥儿》(上卷)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5页。
[9] [法]卢梭著,李平沤译.《爱弥儿》(上卷)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6页
[10] 扎古尔·摩西主编,梅祖培、龙治芳译.《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第四卷) [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第21页。
[11] [德] A.耶格施密特/记撰,张任之/译.与胡塞尔的谈话,《世界哲学》[J]2017年第3期,34页。
[12] [英]约翰·怀特著,李永宏等译.《再论教育目的》[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7页。
[13] [法]雅克·德里达著,朱刚译.《论精神——海德格尔与问题》[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109页。
[14] [德]尼克拉斯·卢曼著,宾凯、赵春燕译.《法社会学》[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8年,第71页。
[15] [德]尼克拉斯·卢曼著,宾凯、赵春燕译.《法社会学》[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8年,第82页。
[16] [德]尼克拉斯·卢曼著,宾凯、赵春燕译.《法社会学》[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8年,第78页
[17] [德]尼克拉斯·卢曼著,宾凯、赵春燕译.《法社会学》[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8年,第82页。
[18] 参见郭贵春、赵晓聃.规范性问题的语义转向与语用进路,《中国社会科学》[J]2014年第8期,第69-70页。
[19] Alan Miller. Understanding People: Normativity and Rationalizing Explanation[M],Oxford: Clarendon Press,2004.P.83-4.
[20] Alan Miller. Understanding People: Normativity and Rationalizing Explanation[M],Oxford: Clarendon Press,2004.P.92-3.